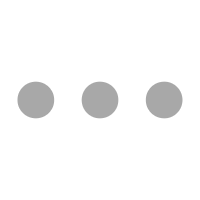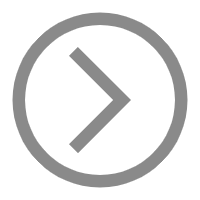今年秋天的朋友圈属于酱香拿铁,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,莫名其妙撞到一起,碰撞出的奇妙反应,让大家好奇不已。 与这种立马可进行的联名概念不同,医药领域要实现不同事物的结合,通常是一个漫长且严谨的过程。就算是非常成功的药物,兼顾疗效和安全性也要历经多年时间来进行验证,还很多药物不能通过。在制药领域,最容易联想到因为组合在一起而产生全新性质的,是抗体偶联药物(ADC)。在还没有精准治疗的时代,人们希望能出现一种神奇药物,可以只选择性作用于肿瘤部位,而对正常部位没有影响。这就是所谓神奇“魔法子弹”概念的来源。但和“美酒加咖啡”这种立马可进行的惬意闲适不同,ADC药物实现“魔法子弹”的概念,经历了制药界长达百年的努力,才实现了靶向药物选择性和高活性细胞毒药物杀伤性的可控结合。 图1. 单抗靶向特异性+高活性细胞毒药物强杀伤性=ADC药物 ADC药物的发展,根据技术发展和问题解决,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,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一些差异,一般认为截至目前经历过三个时代,从早期概念的提出到初步验证,再到第一代、第二代和新一代ADC药物的推出。 图2. ADC药物百年探索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(概念验证) 90年,对ADC药物的概念认识逐渐成熟 很多人将ADC药物的概念提出追溯到德国科学家Paul Ehrilch,1913年其提出“Magic Bullet”的想法。但Paul Ehrilch只是提出特异性作用于肿瘤的概念,并没有指出采用什么技术去实现,当时抗体技术都尚未成熟,更谈不上ADC药物。 直到1958年,出现第一次对ADC药物概念的验证,当时法国科学家将甲氨蝶呤通过重氮反应偶联至从仓鼠血液提取的γ-免疫球蛋白,并在白血病细胞系中进行了抗肿瘤作用测试。但由于当时抗体来自于动物提取,分离纯化非常困难,因此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和试验。 1970年代,随着单克隆抗体技术的出现,抗体制备问题得到解决,从而产生第一批早期ADC药物,这些ADC药物在临床前试验中观察到能在肿瘤部位的富集,不仅进行了人源肿瘤种植动物模型的研究,而且开始进入临床试验。1983年,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的科学家首次报道将靶向癌胚抗原(CEA)的抗体和长春地辛偶联形成的ADC药物在人体进行临床试验,通过放射性标记和安全性观察证实ADC药物的可行性。美国Scripps研究所的科学家将抗上皮黏附分子(Ep-CAM,多种实体瘤有表达)抗体KS1/4与甲氨蝶呤和长春碱以不同化学键偶联形成多个ADC药物,并进行临床研究,可惜均止步于I期临床试验。 同时期的BR96-Dox(靶向Lewis Y),是第一个进入II期临床试验的ADC药物,并显示相比未偶联的多柔比星,BR96-Dox具有完全不同的药代动力学性质。1993年百时美施贵宝(BMS)公司曾报道BR96-Dox在人肿瘤移植模型中显示出治愈潜力,引起广泛关注。但嵌合抗体的免疫原性和偶联技术的不成熟,由此引发的严重脱靶毒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BR96-Dox和其他早期ADC药物一样以失败告终。这些早期ADC药物,对这类药物的概念进行了验证,尤其是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出很好的抗肿瘤作用,但却因当时采用的抗体技术(鼠源抗体)和载药(传统化疗)的限制,最终在临床试验中未显示出有意义的应用价值。 第二阶段(技术优化) 10年,解决均一性和不稳定的问题 通过从早期ADC药物的体内外研究中吸取经验,并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,2000年,第一代ADC药物得以问世,由此拉开ADC药物应用于临床实践的序幕。但第一代ADC药物存在很多不足,以惠氏(后被辉瑞收购)和Celltech(后被优时比收购)的CD22靶向ADC药物——吉妥珠单抗(Mylotarg)为例,其采用酸敏感性连接子,容易受到体内酸环境影响而过早裂解,因而脱靶毒性较高;并且吉妥珠单抗的均一性很差,其产品中50%的单抗携带载药量的药物抗体比(DAR)是1-8的混合物,另外还有50%是未偶联任何载药的裸抗体,这些未携带载药的抗体或携带不同量载药的ADC药物会竞争性结合作用靶点而使其疗效降低。这些因素都导致吉妥珠单抗的临床获益有限,且具有致命毒性,最终于2010年退出市场。后来对吉妥珠单抗的给药方案进行优化,采用低剂量分次给药的策略提高了其疗效和安全性,但总体而言,其表现仍然差强人意。 尽管2000新千年吉妥珠单抗上市之后的10年时间,再没有新的ADC药物上市,但吉妥珠单抗的遭遇,让研发人员意识到ADC药物质量控制的重要性,将ADC药物研发方向聚焦到提升DAR的均一性和连接子稳定性方面,由此产生新的更加稳定可控的连接子偶联技术,为下一代ADC药物的问世奠定基础。 第三阶段(ADC药物时代) ADC药物相关技术成熟,新一代ADC药物进入爆发期 2011-2020年间,全球范围内先后上市了多款第二代ADC药物,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第一代ADC药物的均一性差和不稳定的缺陷。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为维布妥昔单抗(Seagen和武田公司开发)和恩美曲妥珠单抗(ImmunoGen和Genentech公司开发)。这两个产品的连接子偶联技术,直到今天大多数在研的ADC药物依旧可以从中找到技术原型,因为他们奠定了ADC药物提升均一性和稳定性的方向,是通过使用不可裂解连接子或酶识别切割连接子提升ADC药物稳定可控的代表。尽管相比第一代ADC药物在结构设计上取得进步,但第二代ADC药物技术仍然不够成熟。以T-DM1为例,其连接子不可裂解,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药物的稳定性,但其脱靶毒性仍不可忽视,血液循环中的脱落率达到18.4%。并且因其在肿瘤细胞中释放的载药复合物Lys-SMCC-DM1携带电荷,难以穿透细胞膜,不具备旁观者效应,这意味着针对异质性肿瘤不能发挥杀伤作用,因而在克服肿瘤异质性耐药方面缺乏疗效。不仅如此,第二代ADC药物的均一性存在提升空间,由于偶联技术和稳定性的限制,形成的是不同DAR和不同位点偶联的混合物,平均DAR范围一般为2-4,T-DM1的DAR为3.5,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抗肿瘤作用较为有限。 由于概念验证和早期技术积累已经完成,并存在明显的优化空间,2018年前后更新一代的ADC药物应运而生。在已上市第二代ADC药物的基础上,新一代ADC药物在多个方面取得突破,成熟的抗体技术、新型载药、更稳定可控的连接子和多样化的偶联技术,同时也有更多的靶点被鉴别出来。由此,获批上市的ADC药物逐年增多,多个肿瘤治疗领域进入ADC药物时代。 掀起新一代ADC药物的百年革新浪潮 新一代ADC药物的代表是德曲妥珠单抗(T-DXd, DS-8201),它的出现使ADC药物直接成为抗肿瘤治疗的主流药物,进入新一轮的研发浪潮,如今各家制药公司几乎都有ADC药物在研。有数据显示,全球超过350款ADC药物正在进行研发,中国仅HER2靶向ADC药物就有超过30款产品处于不同研发阶段。T-DXd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,成为制药行业炙手可热的话题。 图3. 全球和中国ADC药物管线分布(数据来源PharmaCube T-DXd由抗HER2单克隆抗体和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通过基于四肽的可裂解连接子偶联而成的新一代ADC药物。从药物设计和作用机制上看,具有以下独特属性: 图4. 新一代ADC药物T-DXd的结构特征 抗体部分与曲妥珠单抗氨基酸序列一致,保留曲妥珠单抗的生物学活性,其与HER2蛋白结合的亲和力以及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(ADCC)不受影响。 药物抗体比(DAR)达到8,突破了传统ADC药物DAR仅为2-4的限制,大大提高抗肿瘤活性。T-DXd采用半胱氨酸偶联方式,在特定条件下,由lgG1抗体4个链间二硫键还原而成的8个半胱氨酸残基被全部偶联,得到DAR高度均一的ADC产物。此外,T-DXd采用优化的四肽连接子,其结构中引入亲水性基团,有助于减少ADC药物的聚集。因此T-DXd表现出良好的药代动力学特性,在DAR达到8的情况下也不会被快速代谢。 连接子在血液循环中高度稳定,在人血浆中,DXd在21天的脱落率大约仅为2%。但内吞至肿瘤细胞内后,可被其中高表达的溶酶体蛋白酶特异性识别和切割。这些设计有助于降低T-DXd的脱靶毒性。 载药DXd为高活性的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,具有强大的抗肿瘤活性,是SN38(伊立替康活性代谢产物)的10倍,约为传统化疗药物的1000倍。由于这类细胞毒药物与乳腺癌常用的化疗药物(如紫杉醇)机制不同,能有效避免与化疗的交叉耐药,且有研究表明DXd对P-gp高表达的肿瘤(化疗耐药常见机制)仍然有效。 此外,载药DXd还具有良好的细胞膜渗透性,能发挥强效旁观者效应,不仅能杀伤HER2高表达的肿瘤而且对邻近不表达HER2的肿瘤也有杀伤作用,因而能在更广泛的HER2表达水平或异质性的肿瘤中发挥作用。 ADC药物从概念提出到临床应用再到技术成熟,整整超过100年的探索历程,期间抗体制备纯化、蛋白质工程、药物化学、蛋白质分析表征等各项相关领域取得长足发展,为ADC药物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。1+1>2的美好设想,ADC药物领域的几代科学家用科学技术累计的方式走过了百年历程,如今终于成为制药行业竞相追逐的领域。但在T-DXd掀起的ADC药物新浪潮中,众多在研ADC药物是否能重复其成功,仍未可知。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依旧驱动着这个领域在持续发展。 参考文献: 1.Yiming Jin et al. Pharmacol Rev 74:680–713, July 2022 2.R. V. J. Chari et al. Angew. Chem. Int. Ed. 2014, 53, 3796 – 3827 3.Nakada T, et al. Chem Pharm Bull (Tokyo). 2019;67(3):173-185